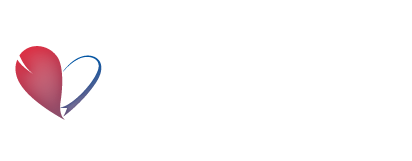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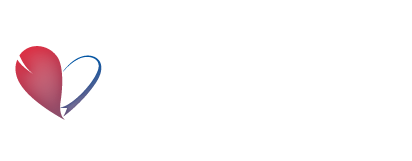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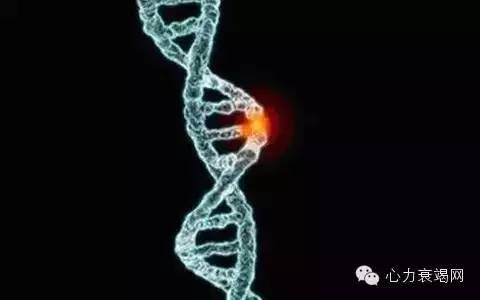
“经过5年的努力 ,基因活性调控的开关终于找到了,肺癌、乳腺癌等困扰人们健康的癌症治疗有了新思路。”近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IBS)蓝斐教授兴奋地告诉澎湃新闻:“乐观地估计,再过5年左右,根据这一研究而研制出的新药将会上市。”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IBS)蓝斐教授实验室和施扬教授-石雨江教授实验室合作取得的这一最前沿的新发现,于4月7日被全世界最权威的三大学术杂志之一的Cell杂志刊发。
上述研究发现,在癌细胞中,染色质中的增强子失控,会过度强化附近癌基因的活性,导致细胞异常甚至癌变。研究同时发现,出现在该区域的蛋白质RACK7和去甲基化酶KDM5C可以限制此类增强子的活性,使基因表达保持在正常范围,从而抑制癌变。
基因突变并非生物体性状改变唯一原因
半个多世纪前,科学家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作为细胞中主要遗传物质的基础,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DNA上携带着遗传信息的片段,通常被称为基因。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DNA序列发生着缓慢的变异以适应着环境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依据达尔文的学说,认为生物体的性状改变是由于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造成的,这样的改变剧烈且不可逆转。
然而,真实情况下,生物体适应外部环境的速度远高于基因突变速度,这说明很多生物学现象的变化速率远高于DNA的变化频率,仅靠DNA序列本身无法完全应付外部环境变化。
事实上,作为遗传物质载体的染色质上还有另一种物质——组蛋白。组蛋白缠绕着DNA链,支撑和保护着DNA。它们在稳固基因组的同时,也调控着基因的表达:通过改变相关因子的活性来改变DNA信号的释放,控制遗传数据库的输出,进而调控生物体的外在性状。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组蛋白的作用就是稳定DNA,不具太多研究价值。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研究者发现组蛋白上的化学修饰可能具备开关功能,能够控制基因的活性,组蛋白修饰的重要性才因此被确定。
为基因活性找到调控“开关”
蓝斐教授研究团队和施扬教授-石雨江教授研究团队的此次发现,就好比在组蛋白上为基因活性找到了一个调控“开关”。
组蛋白甲基化是一种普遍而关键的修饰形式,它的功能就像是为DNA“贴标签”,来告诉基因组一段段特定的DNA序列如何编码、有什么作用。此次研究的对象——发生在组蛋白H3第4位赖氨酸(H3K4)上的甲基化,就是用来标记该区段DNA活性的。该赖氨酸可出现多种甲基化状态,一般认为其高甲基化态(H3K4me3)出现在基因的起始区,而低甲基化态(H3K4me1)则标记着增强子区。增强子虽然本身不是基因,但是对附近基因活性调节至关重要,增强子失控可直接导致其附近基因活性失控。
复旦大学的这项研究意外的发现,H3K4me3也能发生在增强子区,标记着增强子的过度活化状态,并增强附近的癌基因活性和细胞转移能力,易造成癌变。 研究组顺藤摸瓜,找到了一种名为RACK7的蛋白质,它可以吸引名为KDM5C的组蛋白去甲基化酶,将原本的高甲基化状态转化成低甲基化状态,使周围的基因表达保持在正常范围,从而阻止细胞癌变。
增强子活性调控机制可应用于癌症治疗
据蓝斐介绍,这项研究早在2011年就已启动,起初进展并不顺利,“这个RACK7蛋白像是藏于通幽曲径之中,我们知道那背后是壮丽的奇景,但始终不能得窥门径”。直到2014年初,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生物医学研究院博士后沈宏杰和博士生徐文绮意外地发现“增强子过度活化态”并证明其与RACK7之间存在关联,这才“摸准了脉”,之后的研究也水到渠成。
实际上,由于改变增强子活性比改变基因序列更容易实现,因此具备极大的应用前景,它已成为近年来表观遗传领域的一项研究热点。只是在这项新发现以前,学界未意识到H3K4的甲基化动态变化发生在增强子上,因而并未发现该调控的具体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哈佛双聘教授施扬正是组蛋白去甲基化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早在2004-2007年间,他与当时还在其实验室开展研究的石雨江博士后和蓝斐博士在国际上发现了首例组蛋白去甲基化酶LSD1和其它多类去甲基化酶,包括本项研究涉及到的KDM5C。去甲基化酶的发现,不仅证明了组蛋白甲基化是可逆的,也为甲基化修饰参与基因活性的动态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
12年后,蓝斐教授研究团队和施扬教授-石雨江教授研究团队的这项发现,又将该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蓝斐笑言:“那时候只知道组蛋白甲基化是基因组上的‘标签’,‘标签’可贴上也可以撕去,但是很多‘标签’的具体功能并不清楚。通过这些年的积累,已经知道越来越多的‘标签’是在做什么的,还知道是哪些因子在什么情况下在‘贴’和‘撕’它们的了。”
这项发现,不仅发现了表观遗传修饰对基因组信息进行自我调节的新规律、提出了“增强子过度活化态”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潜在的医疗价值:很多癌症病例中存在RACK7和KDM5C突变现象,无法对增强子活性进行限制,使得本应保持低活性的基因异常活化。如今这一机制被揭示,不仅对癌症发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更可为癌症的个性化治疗提供新的药物靶点和治疗思路。